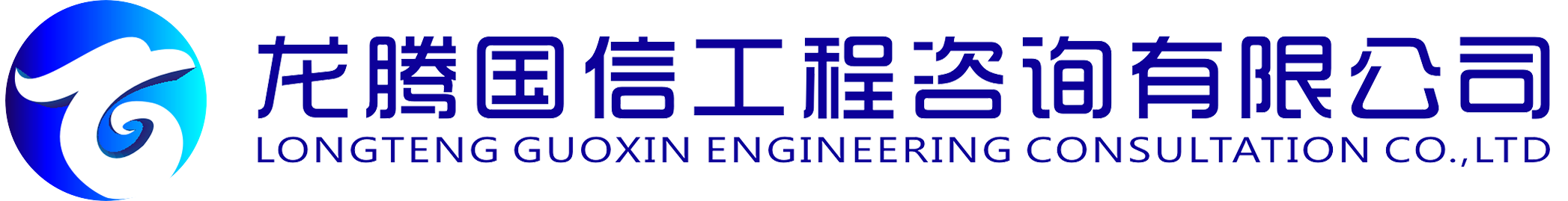- 歡迎訪問龍騰官網!龍騰國信是專業的工程審計和造價咨詢公司,具有甲級造價資質的全過程造價事務所,業務涉及BIM項目設計,工程造價鑒定,預算編制,工程竣工結算,招標代理等。合作熱線:李主任 158 7325 3255
防止特色小鎮“房地產化”,政策監管層面該如
龍騰造價 l 2018-07-05 08:22:29
特色小鎮,從倡導至今,雖只有兩年時間,但其繁衍與變身的速度卻格外迅猛。此前,上市公司華大基因聯手蘇州高新、萬科等房地產企業借打造生命科技小鎮之名,從而套騙國家高額補貼與土地的實名舉報信,暴走整個網絡與平面媒體。
盡管事實的真偽有待驗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全國各地正在快速上馬與大面積鋪開的特色小鎮不應成為房地產商刨金掘銀的樂土。
但是,透過加速跑量的特色小鎮,我們很容易從中捕捉到許多房地產商身影,如碧桂園在廣東惠州打造的科技小鎮、華夏幸福在河北廊坊布局的幸福創新小鎮、萬達在江蘇和遼寧等地主推的旅游小鎮,此外還有綠地在京津冀區域推出的智慧健康小鎮等等。
目前來看,無論是龍頭地產商還是中小型地產商,均不約而同地投身到了特色小鎮的布局與建設熱潮之中。而地產企業投資特色小鎮除了有惠及一方的暖意與情懷,更多的是逐利的商業動機。
如今,房地產企業集體奔向特色小鎮,主要是一二線城市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拿地成本也越來越高,而且針對虛高房價的限購、限貸、限價與限售等宏觀調控政策接連不斷,并且三四線城市也因房價上漲而納入到了調控的范圍。
與此同時“棚改房貨幣化”安置模式也被叫停,地產商在大中型城市可以轉身騰挪的空間日益收窄,而轉向特色小鎮,不僅可以廉價拿到土地,還能享受到政府的補貼,何樂而不為?
更為重要的是,特色小鎮往往會冠上智能、文旅、科技、健康等時尚與先潮的前綴,成為當下人們提升生活品質的的重要選擇,進而助推價格上漲。
地產商之所以能夠集群式而且非常順利地進入特色小鎮,主要是可以與地方政府的需求實現無縫對接。
在不少地方官員眼中,特色小鎮就是一個投資平臺,借此不僅可以短平快地獲取增量資本,還能制造出供人觀瞻的面子工程與政績工程,于是在特色小鎮建設上定數量、下指標成為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標配動作,而迎合地方政府的平臺融資偏好,房地產開發商也紛紛喊出了打造各種特色小鎮的響亮口號。
然而,依靠房地產來造鎮,且不說在用地規模上定會對其他產業投資形成“擠出效應”進而導致資源錯配,由于地產商缺少產業運作經驗,而且房地產本身也沒有技術含量,結果造出來的特色小鎮必然是一個缺乏實體內容與產業支撐的低端空心鎮。而且說不定樓房蓋起來了,房價炒上去了,地產商獲利走人,最終留給特色小鎮的可能是一地雞毛。
進一步分析,特色小鎮的價值定位其實并不允許在其空間上進行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一般而言,特色小鎮處在城鄉結合部,一方面承接城市轉移出來的要素資源,并通過自身產業的加工分理,朝著鄉村進行路徑最短與效率最高的經濟輻射。
另一方面,特色小鎮面向鄉村構建起農產品加工、分級包裝與營銷,為城市傳遞與輸送產品與服務;不僅如此,特色小鎮還承擔著城鄉信息咨詢、人才培養等服務產業的打造功能,進而促成鄉村一二三產業更好的粘連與融合。
概而言之,特色小鎮作為引領者可以在一個合理的空間范圍里將城市功能和鄉村功能有效融合起來,形成城鄉一體發展格局,進而帶動鄉村振興。而完成以上價值與功能的延伸和傳遞,遠非房地產企業所能勝任,而只有通過特色小鎮中的多主體產業聚集與協同方可實現。
當然,特色小鎮除了健康綠色的生態環境,為人們提供宜居空間,還需要更多人性化的服務設施配置,因此,特色小鎮須配備教育、文化、醫療、環保等多重硬件設施,這樣,特色小鎮也就離不開地產商所開發出的產品供給。
但是,對于房地產企業而言,面向特色小鎮所提供的房屋品種,凝結其上的公益性應當大于商業性,在保持微利的前提下,每個地產商都應盡可能策應小鎮支柱產業的構建以及服務設施的鋪展。
在這里,為了防止特色小鎮的產業“空心化”與“房地產化”,政策與監管層面必須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小而美”是特色小鎮之魅,也是特色小鎮之優,為此,必須制定出嚴格與清晰的開發規劃,圈定明確的區域版圖范圍,決不允許任何企業越界擴建,更不允許房地產商圍繞特色小鎮進行邊界開發。
其次,基于引資與產業構建的客觀需要,特色小鎮應采取地產商+實體產業的進入方式與開發模式,明確出臺一個地產商只有聯手一定數量與一定資產規模的非地產企業,方可在特色小鎮進行商業開發的政策規定。
再次,在特色小鎮推行租售結合與以租為主的住房配置方式,為此,需要明確規定出地產企業可供租售的房屋建造比重;為了防止投機資本的作祟,可運用已經面世的全國不動產信息平臺,對特色小鎮售賣商品房進行限購,從需求端首先抑制房價上漲的苗頭;與此同時,要嚴厲打擊中介機構與投資者聯手炒作房產的行為。
最后,國家相關部門應建立一套針對特色小鎮的動態評價與復盤考核機制,包括特色小鎮中的產業數量以及核心支柱產業的企業集群數目,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比例,非房地產企業利稅貢獻指標等,并及時果斷地叫停地產開發占比過重、產能過剩與低端產業循環的偽特色小鎮,同時,要嚴格控制特色小鎮的數量,在高質量的對標中不斷優化特色小鎮的整體形象。